李霞|诗歌个人化写作走向——以陆健《陆健先生的发呆》为例 ...
诗歌个人化写作走向 ——以陆健《陆健先生的发呆》为例 李 霞
看到陆健这首《陆健先生的发呆》,差点想笑。但一看完,便没有了一点笑意,甚至想到悲苦,但也没有真的悲苦,只是突然就感觉掉进了一片海里。但欣喜的是,陆健先生又有了一首神妙代表作,我们这群中年走向老年的人们,也有了自己的自画像。
陆健先生的发呆
左臂靠近茶几上的烟缸 头部略微右转,朝向窗户—— 陆健先生发呆的标准姿态
太太说的是啊,这姿势 一定格,便更呆,愈发呆
一个星期来过。一个星期过来 多少个日夜没有礼拜
歌哭都淡了。虚妄;实在 他发呆,“呆”的里面 不知所由、不知所以的 多边形的白。空白
“木”字旁边站立的楼、树 “木”字举起的“口”——呆 不语。一阵鸟鸣揉乱他的头发
2025年7月5日,11月3日修改。 一
诗以“发呆”为核,一下刺破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局。“标准姿态”的精确描摹,实则是被规训的生存状态的隐喻——连放空都显得程式化。太太的调侃“愈发呆”点出这种状态的自我固化,而“多少个日夜没有礼拜”更直指精神生活的匮乏与仪式感的消亡。最锋利的是对“呆”字的解构:“木”旁是发僵的楼与树,举着的“口”是失语的呐喊。当“歌哭都淡了”,内在只剩“多边形的白”——非纯粹的空白,而是被现实切割成各种形状的虚无。最后被鸟鸣揉乱的头发,暗示自然生命力对僵化秩序的唯一扰动,但这扰动终究未能打破发呆的闭环。全诗在极简场景里完成了对精神荒芜的解剖,所谓“著名诗人”的称号在此反衬出创造力的枯竭,构成无声反讽。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在于其以极简、冷静的笔触,完成了一次对精神内里的深度勘探,其力量蕴含于克制的反讽、精准的解构与意象的陌生化之中。 其一,场景的雕塑感与反讽的生成。 开篇以近乎白描的笔法,勾勒出“发呆的标准姿态”,如同为一座雕塑定位。这种精确性本身便构成一种反差:连最无意识的“发呆”都被规范化了,暗示了主体高度自觉甚至僵化的生存状态。“著名诗人”的官方导读与诗中“愈发呆”的私人状态并置,形成了标题与内容、社会身份与内在真实之间的微妙反讽。 其二,时间的钝化与精神的悬置。 “一个星期来过。一个星期过来”通过语序的微妙重组,营造出时间的循环与黏着感。“没有礼拜”一语双关,既指失去了时间标记,更隐喻了精神生活中仪式感与神圣性的消亡。“歌哭都淡了”则宣告了情感浓度的稀释,一切归于“虚妄;实在”之间的茫然摇摆。 其三,对“呆”字的意象解构与智性开掘。 这是全诗的诗眼。诗人将“呆”字拆解为“木”与“口”,赋予其全新的意象系统:“木”旁站立的楼、树,是外部世界僵化、物化的象征;而“木”举起的“口”,则成为失语、无言的隐喻。这种文字学的戏仿,将抽象的内心状态“空白”,具象化为“多边形的白”——不再是纯粹的虚空,而是被现实种种框架切割后,充满紧张感的复杂虚无。 其四,以微声打破静默的结尾。 最终,“一阵鸟鸣揉乱他的头发”,是唯一的动与声。这来自自然界的、不可控的短暂扰动,并未真正打破发呆的闭环,反而以一丝转瞬即逝的生机,反衬出那内部沉默的凝固与强大。 全诗如同一场在平静表面下进行的激烈语言学与精神分析,它不宣泄情感,而是通过凝视与拆解“发呆”这一微不足道的瞬间,映射出当代知识分子丰富而荒芜的内心图景。
二
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局,在于其同时承受着多重的剥离与悬置。他们曾被赋予“社会良心”的期许,手握阐释世界的语言权杖。然而在资本与流量的合谋中,知识的神圣性被消解为可标价的资讯产品,深度思考在即时反馈的狂欢里显得笨拙而迟暮。这带来了第一重困境:启蒙者角色的失落与话语的失效。 更深的痛苦源于内在的割裂。他们是概念的巨匠,习惯于用理论框架切割鲜活的经验,却发现自己恰恰是那个最彻底的“异化”样本——精神悬浮于概念的高空,双脚却未能触及生命实感的大地。这种知行分离,使得批判的锋芒在转向自身时变得犹疑而无力,陷入“诊断出疾病,却开不出药方”的智识窘境。 于是,一种普遍的倦怠与“发呆”成为表征。这并非无所事事,而是意义参照系崩塌后的内在停滞。当“歌哭都淡了”,当价值判断在虚无与实利之间剧烈摇摆,行动便失去了坚实的根基。他们被困在书斋与广场之间,在“木”的僵化结构与“口”的失语状态中,守望着一片被切割得支离破碎、不知如何填充的内心“空白”。 最终,困局的核心是一种深刻的无力感,他们能精准地描摹乃至解构困境,却难以在解构之后的废墟上,为自身的精神找到一条确信的出路。
三
《陆健先生的发呆》如同一份精准的“精神切片”,它不仅记录了一个生活瞬间,更标志着他的一种独特诗学风范的成熟:即以极致的“真性纪实”为方法,呈现出深刻的“后现代”精神图景。这两者在他的笔下并非割裂,而是互为表里,共同构筑了一个真实而又虚妄的文本世界。 场景的零度书写。诗歌开篇如同剧本提示,“左臂靠近茶几上的烟缸 / 头部略微右转,朝向窗户”,这是一种剔除抒情和修饰的白描。诗人将自我客体化为观察对象,进行不动声色的记录,这种“冷叙事”使得“发呆”这一私人状态获得了公共的、可被审视的客观性。细节的考据癖。他对“发呆”的描绘不止于行为,更深入其肌理。从“标准姿态”的归纳,到太太话语的引述,再到对“一个星期来过。一个星期过来”这种时间微妙拖沓感的捕捉,都带有一种人类学式的田野记录色彩,真实得近乎残酷。 这种纪实的背后,是一种面对自身真实的勇气。作为“著名诗人”、“教授”,他敢于剥落文化光环,将“发呆”——这一与创造力、生产力相悖的状态——公之于众,并坦然承认内心的“空白”与“不知所由”。这本身就是对“诗人”神话的一种祛魅,是最高级别的真实。在纪实的外壳下,诗歌弥漫着浓烈的后现代气息,主要体现在意义的悬置与语言的自我指涉。 中心的消解与“空无”的核心。后现代主义质疑宏大叙事和深度模式,这首诗正以“发呆”为此作了最佳注脚。“歌哭都淡了。虚妄;实在”,所有强烈的情感和价值判断在此均告失效。诗歌的核心不是某种深刻的主题,而恰恰是那片“多边形的白”——一种被现实框架切割、规训后形成的复杂空无。这不是等待填充的空白,而是意义系统崩塌后的最终现场。语言的自我解构,诗歌最精彩的部分在于对“呆”字的拆解。“‘木’字旁边站立的楼、树 / ‘木’字举起的‘口’——呆”。这不再是传统的意象营造,而是一次后现代式的“语言考古”。诗人将词语打回原形,暴露其构成密码:“木”象征着外部世界的物化与僵化,“口”则象征着内在的失语与无言。当语言本身成为剖析的对象,并反过来揭示主体的困境时,文本便完成了深度的自我指涉,充满了哲学性的戏仿与智性游戏。主体的零散化,诗中的“陆健先生”不是一个统一的、自信的抒情主体,而是一个被观察、被调侃(太太的话)、被外部细微事件(鸟鸣)所扰动的碎片化存在。“发呆”本身就是主体性暂时消散、陷入停滞的状态。这与后现代理论中“主体的死亡”形成了精妙的呼应。 纪实与后现代的融合,在真实的废墟上构建寓言。陆健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并非在玩弄虚无缥缈的文字游戏,他的后现代气息,是建立在坚实、甚至有些笨拙的“纪实”地基之上的。以最真的笔,写最虚的心。 正是那些无比真实、可信的细节(烟缸、窗户、太太的调侃),为后现代意义上的“空无”与“解构”提供了可信度。我们相信那片“多边形的白”真实存在,因为它源自一个被我们确认为真实的场景。个人困境成为时代寓言。 “陆健先生发呆”既是一个严格的个人化纪实,同时又迅速跃升为一代知识分子、乃至所有现代人精神处境的寓言。在信息过载、意义超发的时代,个体的回应可能不再是积极的建构,而是这种被迫的、程式化的“发呆”——一种内在的罢工与悬置。 陆健的写作抵达了一个新的境界,用纪实性的笔触捕捉后现代的灵魂。在他的诗里,真实不再是意义的保证,而是意义消解过程的证据;记录不再是情感的抒发,而是情感耗尽后的冷静测量。这种写作,既是对自我真性的勇敢纪录,也是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空无”,留下的一份冷静、精确而又充满反讽意味的病理学报告。
四
陆健的诗歌写作,呈现出一种在学院派的严谨与生命个体的真实体验之间寻求平衡的探索姿态。他的诗艺根基深厚,这体现在对语言和形式的自觉控制上。从四十多年前的早期作品到近年的创作,能看出他致力于将日常经验进行诗意的提纯,善于捕捉具体生活场景中的瞬间,并赋予其形而上的思考空间。他的一些诗作,如《名城与门》等,展现了将历史、文化沉思与个人观察融为一体的企图。 然而,诗人身份所伴随的学院背景,有时也构成一种无形的框架。他的部分诗歌,在追求意义的深度和表达的精准时,偶尔会显露出被知识体系和文学传统所“规训”的痕迹,即语言和思维在一定程度上被预设的审美范式所塑造。这可能导致某些文本在“完成度”很高的同时,也失却了些许原生性的冲击力与野性。 他近期的作品,显示出一种可贵的内省与突破的尝试。这首诗通过自我解构——“发呆”这一非生产性状态——恰恰触及了当代知识分子(包括诗人自身)的精神困局:在娴熟的诗艺背后,可能面临的创造力的焦虑、意义的虚空以及与真实生命激情的疏离。诗中对“呆”字的拆解,正是对这种悬置状态的精妙隐喻。 因此,陆健的诗歌写作可被视为一个不断自我审视和调适的过程。他既运用着学院派积累的深厚素养,又敏感地意识到这种素养可能带来的遮蔽,并试图通过反讽与自省,刺破形式的完满,去触碰那些更为质朴、甚至有些茫然的内在真实。他的价值,或许不在于提供了某种决绝的先锋姿态,而在于真实地呈现了一个身处文化中心的写作者,在承袭传统与面对自身精神困境时的诚实与探索。
五
陆健的诗歌写作体量绝对是庞然大物,而且视野路宽,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没有不可入诗的。已正式出版的诗集有20余部,其中长诗30多首,但他诗歌的脉象也非常明显,近来的笔离自己越来越近,走向自我,走向个人,走向内心。这也是陆健诗歌创作演进中最核心、也最动人的脉络。这条由外向内由表及里的路径,也昭示了一位诗人真正的成熟与勇气。 早期,在宏阔的景深中定位自我。陆健早先书写生命、历史、文化及文化人,这像是在构建一个广阔的精神坐标系。通过与他者、与历史、与宏大概念的对话,他试图在其中找到并确立“自我”的位置。这个阶段的写作是向外辐射的,是诗人用才华和学识去丈量世界,笔端是审视的、抒情的,有时甚至是代言式的。 中期,在关系的网络中映照自我。将笔触转向朋友、学生、家人,意味着坐标系的收缩与具体化。从“文化”这个抽象集合,转向活生生的、有温度的“关系网络”。在这些诗中,他通过描绘与他人的情感链结、生活片段,来间接地映照和勾勒自身的面貌。这时的“自我”,是反射在诸多亲密关系镜面上的影像,更为生动,也更具人间烟火气。 近期,直面无修饰的个人内心现场。2020年以来,他更多地写自己,已有一批这样成熟的作品,如《鲜花的花和老眼昏花的花》《每天,在自己的葬礼上》《我又一次跌入了自己的深渊》《我是我自己林子里的一只什么鸟?》《七十自况》等等,这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向——从映照回归本源。知识分子写作和后现代写作都定义不了陆健,他只是在中外知识谱系与现实生活的磨洗中成为自己,有意表达自我个人。他敢于将笔作为手术刀,直接对准自己的内在状态,一点也不回避自己内心的茫然、虚空与自嘲。这种“近”,不仅仅是题材的贴近,更是视角的內倾和坦诚度的加深。他不再仅仅通过描述“我做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来定义自己,而是直接切入“我是什么状态”、“我为何如此”的内心现场。 从构建史诗到勘探内心。这条“笔尖越来越近”的路径,完成了一个从“构建外部史诗”到“纪录勘探内心真实”的转变。它需要的不仅是技艺的纯熟,更是卸下头衔与光环、直面自身局限与生命本真的勇气。当一位诗人开始无情又慈悲地书写自己的“呆”与“空白”时,他的写作便获得了一种崭新的、基于深刻真实性的力量。这不再是表演,而是存在的证词。
六
这首诗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个人化写作的深刻启示:真正的个人化,并非书写私人轶事,而是敢于凝视并呈现自身生命中最无力、最“无意义”的真实状态。 首先,它展示了个人化写作的勇气在于“祛魅”。诗人主动剥落“著名诗人”、“教授”等社会身份赋予的光环,将一个“发呆”的、近乎失语的自我置于读者面前。这种对自身平庸、困顿乃至精神空虚的坦然暴露,打破了创作者作为意义赋予者的惯常形象,反而建立了一种基于脆弱和共通的真实连接。它启示我们,写作的真诚始于对自我不完美部分的接纳与审视。 其次,它揭示了个人化写作的深度在于“内窥”。诗人没有停留在行为表象,而是深入“呆”的内部,去勘探那片“不知所由、不知所以的/多边形的白”。这是一种对自身意识流和潜意识领域的直接呈现。它将写作转化为一场向内的手术,提醒我们:最独特的个人矿藏,往往不在波澜壮阔的经历里,而在那些无法被简单定义和分类的、混沌的内在感知瞬间。 最后,这首诗示范了个人化写作的艺术在于“赋形”。它将抽象的内心状态,通过精准的日常细节(左臂靠近烟缸、头部右转)、文字学的巧妙解构(“木”与“口”构成“呆”)以及突如其来的感官介入(鸟鸣揉乱头发)具象化。尤其是“多边形的白”这一意象,将“空白”这种虚无的感觉,描绘成有棱角、有压迫感的实体,极具独创性。这告诉我们,个人化的情感与哲思,必须找到其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才能获得超越个人的共鸣。 《陆健先生的发呆》启示我们:个人化写作的路径,是勇敢地回归到那个卸下所有表演面具的、本真的自我,并以其为原点,用创造性的艺术手法,去勘探和命名那些普遍存在于人类内心却难以言说的微妙风景。 李霞,诗人,评论家,媒体人。198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河南省诗歌创作研究会副会长。第三届中国桂冠诗歌奖评委。出版诗歌及评论集《一天等于24小时》《分行》等。
供稿:原作者 | 编辑:牧 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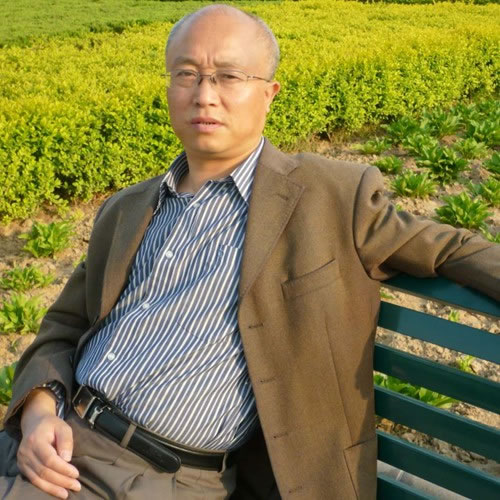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1802003845号
沪公网安备 310118020038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