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巽达 | 在完成自己的同时,抵达文学的纯粹
在完成自己的同时,抵达文学的纯粹 ——读陆萍散文集《床上有棵树》 刘巽达 《床上有棵树》 陆 萍 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对于一位写作生涯50年、算得上著作等身的“老作家”而言,序不序的,已是无关紧要。诗人出版诗集以外的散文集,别有一番意味,那么,我就权当“第一个读者”吧。 我通读了《床上有棵树》的全部篇什,不断被文字中表达的喜怒哀乐所牵引,渐入佳境,时而动容,时而哂笑,时而嗟叹,时而遗憾。这些或长或短的辞章,一篇篇颇似写生,勾勒了陆萍丰富多彩的人生。 散文是一种最自由的文体,它几乎包罗万象,无论是杂记小品或游记随笔,乃至书信日记或史论札记,尽皆收入囊中。陆萍的这本散文集,也是斑驳陆离种类繁多,或是游踪漫笔,或是往事回眸,又或情思记略……至于所涉人与事,更是上自闻名遐迩的名人,下至临刑前的死囚……虽然彼此的身份天差地别,但在陆萍笔下,他们都真实而饱满,因此放在一起阅读,并无违和感,反而能窥得人性深处的微妙与复杂。 她写与名人的交往,素朴而真情,无丝毫忸怩之态。她笔下的徐迟、牛汉、王辛笛、雁翼、赵长天、今辻和典、程乃珊、李小雨、蓉子或章世添等文学同道,亦师亦友,人间烟火,跃然纸上。 这里仅举几例,与读者分享。陆萍写徐迟,那天陆萍陪徐迟同游甪直的保圣寺,在一花草茂盛处,发现了叶圣陶墓地。这时,但见徐迟神情严肃,两眼有光,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口里念叨:“嘿,圣陶!我的老朋友,你在这里啊!今天真是意外的收获!”当同行者纷纷留影后,徐迟说:“陆萍,我想一个人,进去立一歇(沪语:站会儿)。”只见他慢慢上得石阶,站定,再往前走近一步,深情地拍了拍墓碑,又慢慢放下手来,交握在身前,凝视着远方……这位曾与叶圣陶有所过从的老者,瞬间成了一尊雕塑。看到陆萍写的这一幕,我对这位大作家,再次肃然起敬。 写文学恩师谢泉铭时,有一个细节非常具有质感。上世纪70年代,陆萍投稿《解放日报》并求教副刊编辑谢泉铭,由于纺织厂三班倒的作息时间,陆萍只得晚上去报社。她写道,记得有次我看了看表,表示必须立即离开去赶公交车上夜班了。道别时,谢老师声音闷闷地对我讲,陆萍,你以后晚上就不要来报社找我了。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就说上夜班时我只有晚上这点时间有空啊。老师转身回头,就不说什么了。我不明就里,后来我照旧去。直至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晚上去”,惹得对谢泉铭的流言蜚语满大楼飞,莫大的屈辱,泼洒到他身上。这世界的不公不平,至今想来,都变成了我们的敬意…… 上海乃至全国的作家中,被谢泉铭“恩泽”过的作家不少,我读过他们写恩师谢泉铭的文章,但陆萍的描写特别有冲击力,彼时那个圣洁无瑕的姑娘“不明就里”对恩师造成的伤害,读来揪心。这种回忆,具有无可替代的珍贵性。 读陆萍散文,得知现实生活中的陆萍时有某些“低能症状”,比如她是十足的路盲,甚至差点在印度的机场弄丢了自己,某日还会被大枣核卡在喉口,等等。但很多艺术家都有这个通病,他们专注于自己的所好,在钟爱的事业上,不但不“低能”,相反是很“高能”。陆萍也许正因为她执着于文学,才让她无暇他顾,一心直奔心目中的高地,诚如老诗人谢其规所言:“上海的女诗人中,目前算她的诗龄最长了。”确乎如此,她愈战愈勇,而且脱胎换骨。不但在新时期里诗情喷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和众多粉丝,而且接二连三出版的诗集、散文集,得到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资助;更是有陌路诗歌研究者陈胜辉25万字专论《陆萍诗歌赏析》的出版。她那股澎湃的激情,俨然与她的年龄不相符。 陆萍的身上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尘烦俗虑似乎从来不在她的考量中,她永远在不同寻常地凝视、观察、倾听和思考,一如她篇章的这些句行: 选择写诗,是因为诗考量灵魂。诗的精细与锐利,可以无尽层面地触及造物设计的奥秘……能尖锐地体悟日常,潜走人性,感受生死之间甚至时空之外。(《我为什么写诗》) 这旷世之俗,粗野而温和,毛糙而紧密;真可谓是奔而不放,忠而不诚;破而不坏,崩而不溃。这就是一个民族的道德质地和道德场域……(《人性的裸奔》) 凄美的枯树,是黄石一大景观……在强烈的阳光下,呈一种凄绝之美。它或蜷曲一团,存心孤绝世界,或坚挺站立,怒指苍穹……它不诉说,也无话可说。万千惊心动魄、妻离子散、哀痛绝望的故事,它全部经历了、承受了,而且消化了。置身现场的我们,没有缘由,却会那样地揪心生痛。(《生而为人的入世礼》) 除了逼真,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正弥漫其间、濡染了四周,让你看了再要看,让你不舍离去。到底是什么东西吸住了你的魂魄呢?摸不着,看不见,但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得到。我觉得那就是画家将这一切,都悄悄赋予了神性。(《读画速记》) 这些置身于文化景观中的思考,让哲思浑然于景事之中而成至理,是文学的精神滋养了她。在这本书里,“小情调”和“大感情”和谐共振。“小情调”只是一种形容,指的是陆萍笔下无处不在的惊喜和发现:生活中一旦有所触动,陆萍就会让文字伴着思考相拥起舞,接触尘埃却又能够清水洗尘,生发出的哲理感慨,也让读者产生共情。而“大感情”的提法也是一种指代,是那些关乎生死或人性深处的苍茫复杂,这部分的作品令我最为心动。 比如她对印度诗人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就写得很美——面对中国女诗人的诗作《冰》,印度诗人的眼里泪光盈盈,情意浓浓,但他们的“我爱你”,只是一种给予,并不是索取。由此陆萍喟叹:“如果说,我曾经在生活中失落过什么,那么这一天,我在泰戈尔故土上得到的报偿,加倍丰厚;如果说,诗歌创作是幸福的,那么这一晚我体验得最为深刻。”艺术是人间最高的圣地,生命中所有的失去与沉落,想必她都会在文学中寻得与找回。这或许就是她半世纪来矢志不渝,痴迷文学的渊源。 还有,她写到一个判死缓的女死囚,虽然是“罪案”,可是案子里蛰伏着的爱恨情仇,也折射着普通人的人生。更有她现场目睹了一名女重刑犯刑释时的情景,因为长年的监禁,已与社会脱节,年轻女警官取出了几张钞票,和颜悦色地对她说,这是一张10元的钱,一个“0”,还有100元的钱,两个“0”跟在“1”后面。女警官又特意“嘣”的一声落下个东西来,说,这个“钢镚儿”就是一元钱,等于从前100个一分钱的小角子……陆萍写道:“我很感动于女警官于一瞬间的角色转换,前一刻还是她们眼中不可越雷池半步的囚犯,这一刻便是社会上一位孤陋寡闻的老大妈了。” 这些“不可多得”的题材中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有时甚至是作家的“独门秘籍”——萧乾独特的“战地记者”身份,才使他写出有别于他人的佳作;季羡林对身处时代的真实记录,才让他写出了对一段生活的赤诚回忆……本书中有关陆萍的“铁窗文字”,都非常生动感人,也是此书的一个特色。 我特别感喟的是,面对陆萍这个“年轻的老作家”,我觉得她几乎是“与时俱进”的一个生动注解。本书中有一个细节给人启悟:中国台湾的诗人和陆萍在韩国举行的“亚洲诗歌研讨会”上相遇相聚,他们无话不谈,十分投契,并知道亚洲诗坛激赏她的诗作,东道国出全资盛情邀请,并处处给予她“五星待遇”,甚至还为她一人改签机票留客数日。台湾地区的诗人坦陈,他们奇怪于陆萍生活在1990年代,写出的诗却像是1930年代里的感觉。 陆萍如是说:我看重人的生命悟觉,敬畏自然直视天性。因为人类最本质的感受都是相通的,凡文字出自人性幽闭的深处,大都可以通走古今贯穿时空,而成为永恒。 一如陆萍在这本散文集中的那些篇目:《庆祝过往生命》《悬空寺》《我为什么写诗》《清空归零》《神在》《了知生命的大纲》……这些来自存在的本真与灵魂深层的文字,内涵深邃,神秘直觉,情感饱满又哲理充盈,自然就能与任何文化背景之下的读者一脉相通。 她以前的很多著作我也拜读过,尤其是她充满人间大悲悯的铁窗文学,正如她所言,是“摸着人性人道、生死爱恨这些永恒的暗巷子进去”的,真实的血肉全在里面,逼近人性,独具一格。她在完成自己的同时,抵达了文学的纯粹。 回首看去,当年的陆萍曾经非常荣幸地在特殊年代被“海选”成功,全国隆重播发的十首革命歌曲妇孺皆知,其中一首词作者就是她。这在当时,已然属于莫大的“文学成就”了,但她并没有沉浸在年轻时的成功中,而是循着时代发展、人生阅历的增进和深拓,听从生命内在的召唤,去寻觅存在的本真与生命的奥义,将自己的思索与视野去抵达无垠的天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的写作已摈弃了世俗的功利,只为灵魂的平静与安宁,这种低至尘埃的写作姿态,恰恰是文学创作获得成功的秘诀和妙谛,也成就了“活在当下”的陆萍。 而今功成名就的她,仍然跋涉在文学的路上。文学于她,已契进其血肉生命,与她的脉动、心跳、精气与神息,几近合一。相信她一定还会给读者带来惊喜。当生命的觉悟化为笔下诗文时,一切皆有可能。 来源:文汇报 责任编辑:牧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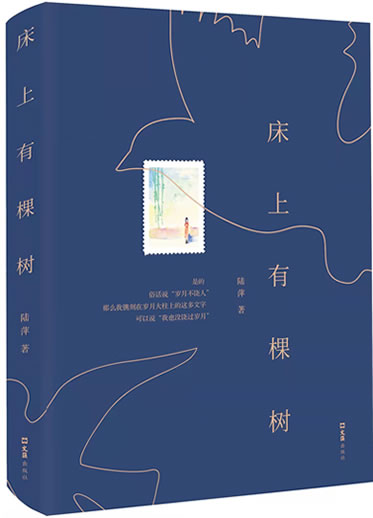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1802003845号
沪公网安备 31011802003845号